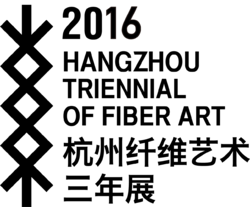一
此刻,我在编织一篇有关纤维艺术的文章。
我敲打键盘,码字,在字里行间穿行,打捞着不断涌现的思绪与词语。刺字,纹身,肉身感知,我编织着文本、图案与意义。
记忆在四周弥漫。写作,也是文字的构造与编织。
万千思绪,如何集腋成裘?《晋书•潘岳传论》有言:“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多有意思,古人爱用贴身可感的丝绸布料来形容与描绘自己的思想感受。甚至对山川与大地,也以“锦绣河山”来加以形容。锦绣,就是精美鲜艳的上等丝织品啊!
二
构造,即编织,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语fabric,这是一种缠绕繁复的时空经验。当我们说“面对”纤维艺术的时候,会意识到“面对”这个词,不够准确,不够生动。纤维艺术作品总是经由日常的生活体验与身体感知,编织出某种场所与空间,让人浸身其中。此刻的我,就沉浸在一个恍兮惚兮的世界中。
实际上,每个人,以及每个人所置身其中的时空,已然是先天性的“织物”现成品。有文字记载:“女娲引绳在泥中,举以为人。”这显然是先人对于人类命运与存在的想象,编织而成的绳子,从泥水中抽出,粘带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人的生命,原来也是一种“织物”。古人又把绳子想象为蟠曲的蛇龙,并在图像世界里不断创造出蟠结的龙神形象。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其中就充满了交织盘曲的龙蛇形象,全是古人世界里的生命意象。
万曼(马林•瓦尔班诺夫Maryn Varbanov)在笔记中曾写道:“毛线材料是有生命力的,它在人的环境中有机性地存在。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表现”。我们的肉身,如此长久地被置于编织空间之中。只要静心反思,就会意识到,从有形的衣服,到无形的网络……我们不只是面对纤维的世界,我们自身就是纤维艺术的一部分。女艺术家刘佳婧的作品《被放大的时间》,就将编织行为与时空之间那种潘多拉魔盒般的衍生关联,带入了展厅现场。
三
最初,人类结绳以记事。在文字发明前,结绳,编织出有意义的符号,就是人类所使用的一种记事方法。中国古老的书籍《易•系辞下》记载,先民在一条绳子上打结,其意图是用来计数或者记录事件发生点,以便通过结绳数来提醒记忆。据各种研究发现,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上古时期的中国、秘鲁、印地安都曾用过,甚至在现代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依然还在沿用。今天,古代秘鲁的编织技艺,印第安人的编织方法都还在现代的纤维艺术中被重新使用。
编织,作为这种技艺,一直保有与我们记忆的亲密感。“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编织行为与母体世界(Matrix)如此无间地缝合在一起。我们知道,Matrix的本意是子宫、母体、孕育生命的地方。这个概念来自数学,又被称为“矩阵”,用来表示统计数据等方面的各种有关联的数据。Matrix代码制造世界的数学逻辑基础。在电影《骇客帝国》中,Matrix被表现为不仅是一个虚拟程序,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世界交织而成的世界。
在很多地区,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着娘家的各种手织女红,带着母体的记忆与祝福,开始新生活。《易•系辞》所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用其祈福来年的平安富贵。”母体的记忆与祝福,以“结绳”的方式予以传递。
在《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中,写到宝玉将祖母赠送的珍贵雀金裘烧了一个洞,而第二天宝玉要穿着见客,故大为着急。无计可施之际,发烧生病的晴雯熬夜把雀金裘补完,却由于劳累过度,晕了过去。这一回中,曹雪芹将“勇晴雯补裘”这个编织的情节描写得惊心动魄,情深义重: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
晴雯一针一线,针针都是情到深处。晴雯死后,宝玉回忆起自己与晴雯的深情,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诔》长文相祭,还特意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副楷字写成。这冰鲛縠,就是用细纱织成的皱状丝织物,很是珍贵。据说,汉代人说的“雾縠”,南朝人说的“天衣”,应该就是这种冰鲛縠了。诗人屈原在《楚辞•神女赋》也曾写道:“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这些记载,足以见出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对于精美织物的深深情怀。
四
纤维艺术,是门古老的技艺,甚至很难用今天这个“艺术”概念来予以描述。从来就没有大写的“艺术”,从来只有艺术家。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断言,在当代纤维艺术这里却似乎不言自明。编织是我们人类亘古以来一种本能,而纤维艺术,一直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与被大写化的艺术世界之间,神秘地维系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最初,我们人类结绳以记事,传递意义。然后,我们学会编织语言文字与图像符码,相互沟通。现在,手机与网络成为身体的延伸,信息传输与智能联接……编织而成的记忆,在我们的肉身深处与生活世界,反复沉淀,成为语词与图像,以及更多仅可默会的不可言说之物。
万曼先生曾一再强调这种古老技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编织艺术领域中人类保存了古代文明的无价作品。几千年前,埃及人已用毛线和织布机来再现不同人体。几千年以前,在尼罗河两岸,埃及人由于需要装饰其衣服并使灵魂更富足发现了编织艺术的美丽……很多诗歌表示,公元一世纪时候,中国的编织艺术非常完美。”万曼还写下了自己的艺术预感:“20世纪末,古代艺术传统很丰富、对人类文化做出伟大贡献的东方地区存在着一种潜力。在文化传统最丰富的东方国家——中国,通过现代画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成为现代挂毯艺术的一个世界先锋中心。”
这种观念,成了中国现代纤维艺术家的一种内在自信与自觉。万曼的学生施慧,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挖掘着棉、麻、宣纸、纸浆的表现力。日常生活世界里最为常见的材料,被素朴而寂静的诗意方式,表现得纯粹而有力度。
在上个世纪“八五”新潮中,施慧与他的几位同学,已经冲刺在国际当代艺术的舞台了。1986 年,在万曼的指导下,中国美术学院制作了多幅壁挂送选“洛桑第十三届国际现代壁挂双年展”,谷文达的《静、则、生、灵》,施慧、朱伟的《寿》,梁绍基的《孙子兵法》三件作品最终入选。果如万曼所预感的那样,几十年过去,施慧在古老与现代的浩繁“编织”工作中,始终能够保持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力。
与材料的共生,对物性的信任,这个传统而又现代的观念,成为纤维艺术家的某种天性。这个看似当代观念的“现成品”,对于纤维艺术而言,却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编织”本身,正是纤维艺术的元语言。美国纤维艺术家希拉•习克斯(Sheila Hicks)表示,自己在做纤维艺术作品时,会有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自由地创作和表达自己意图,并不需要临摹平面绘画的模式或结构。她信任自己的编织行为,是编织行为直接构成了编织世界,在编织的过程中,作品才得以呈现于完成。
五
如同蚕茧之生成,编织的确造就了一种自我的庇护所。《荷马史诗》记载,特洛伊战争结束,奥德修斯十年海上漂泊,漫漫返乡路。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以给公公拉埃尔特斯编织寿衣为借口,拒绝各种求婚。她白天纺织,晚上又拆掉,不断地拆解重织,最终迎来了丈夫的回家。佩涅洛佩的编织,如同蚕茧之成,造就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也是对丈夫奥德修斯的思念与记忆的世界。这种记忆的技艺,使她在漫漫十年的时间里,仍然能够情深义重。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意外闯入桃花源的渔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渔人或许也会打结来处处志之,但仍然找不到通往桃花源的路。我更愿意把这个情节视为一个隐喻,一个关乎人类记忆的隐喻,一个人类失去桃花源记忆的隐喻。
这是符号世界的悖论。
结绳记事,所包含的不只是所谓的信息,不只是储存在硬盘里的知识,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人的经验,是活生生的知识。今天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自己所编撰的知识世界里,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世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的诺顿系列讲座中提醒我们:
在今天,我们受大量形象的疲劳轰炸,我们已经不再能够把我们的直接经验和我们哪怕在几秒钟之内看到的电视内容区别开来。记忆当中,鸡零狗碎的形象的片断像一大堆垃圾一样,在如此众多的形体中间,越来越不可能有哪一个形体能够实现。
卡尔维诺在美国做此系列“备忘录”讲座,是因为他日益担心:语言的传统在千禧年之后被人遗忘,人们开始忘记怎样用语言表述感情。写作也无法再展露人内心的秘密,这些秘密如神秘之物被深藏于地下,再也无从找寻。”我们从结绳记事开始,就试图编织与维持自身的记忆。但这“结”,也可能成为“死结”。精神医疗学上也用“结”来形容看似遗忘却未曾消失的记忆。事物与记忆最终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个读不懂的“死结”,一个个存留在潜意识里永远打不开的“死结”,成为“意缔牢结”(ideology)。今天人工智能的信息编织突飞猛进,但仍然不能替代人类的记忆能力与技艺。法国哲学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曾在其策展的《记忆的灼痛》中写道:
记忆同样在燃烧:记忆不能被削减为彼此相对、冰冷排列着的回忆的集合……记忆使过去的事物重新处于生机勃勃而又紧迫万分的热度之中。或者,记忆会烧毁一切并让我们变得疯狂,如果我们不能将其能量转换为一种自由的实践的话。
这无疑是当代纤维艺术所面对的现实境遇。从结绳记事到纤维艺术,记忆的技艺始终面对着各种危机与挑战。纤维艺术在自我身体感知的层面,关联着从肉身-皮肤-织物-社会的结构。这些层层传递与延伸的时空, “如果我们不能将其能量转换为一种自由的实践的话”,同时也会成为遗忘装置。而纤维艺术,牵系着肉身与都市的多重时空,也注定要被深深卷入这个消费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难题中。
从建筑、街道,到大城市、大都会的构造,本身就是一种编织,一种繁复地地理与社会空间的编织。构造,即fabric,其实就是织物,恰是今天所有大都会的根本形态,是地图上的阡陌交通与星罗棋布。这种构造,在今天的城市形态中,既呈现为景观,同时又呈现为废墟,既呈现为纪念,又呈现为遗忘……在种种相互关联,同时又逆反为相互隔绝的情境中,当代的纤维艺术何为?!
万曼在中国的广阔社会情境中寻找适合的材料,寻找他艺术世界里的麻绳。换言之,他沿循绳索,作为线索,得以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深层世界,以此呈现这个国家本身的诗性文化。在万曼那里,艺术的“诗性”不是来自于高于自己的时代精神,或一个他者世界,而是来自于创造着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是在同具体的物,同现实社会情境中的材料打交道与劳作中呈现出来,是活生生的记忆。
六
拯救或逍遥,这是一个问题。
存在,即是一个迷宫。对纤维的感知,也就是对于无限之线的时空体验。这种体验是人类诞生就有的一个本能,深藏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深处。人如此,山水万物宇宙亦如此。我们常说山水如画,而山水一旦真入了画,有时候锦绣山河不仅成不了残山剩水,甚至会成为一堆没有生气的俗气图案。黄宾虹先生才会说,看山见骨髓,才是真山人。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希腊神话。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依靠阿里阿德涅线团的引导,得以顺利逃出迷宫。看起来,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渔人不同,深陷迷宫的忒修斯王子,被阿里阿德涅线团激活了记忆。古希腊哲人有言:“向上的道路与向下的道路,是同一条路。”失去活生生的记忆,我们或许就会失去这条道路。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在我看来,《齐物论》中所写的“庄周梦蝶”,显然还有另外一种意味:人不仅有造茧而居的能力,同样也有破茧而飞的技艺。方梦方醒之际,前生来世之间,唯有那些深味记忆之技艺的人,才能够得“物化”之功,无往而不自得,不会丧失掉对于事物与世界的鲜活感知。此刻,浮现在我脑海的,正是施慧的纤维艺术作品《本草纲目系列》。被遗忘在中草药世界里的那些植物身体,花花草草,经由艺术家的素朴劳作,重回自然生命的世界之中。用施慧自己的话来说,逝去之物,获得再生。
七
写作,码字,我编织着文本、图案与意义。
这也是一种对于失去时间的寻找,对于记忆世界的重拾。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伟大小说《追忆似水年华》(Se souvenir du passé),有人认为应该翻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更为准确。
失去的,逝去的,如何能够存在?
终其一生,阿比•瓦尔堡都在关注图像传播与意义变迁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沉迷于编织一部奇妙的《记忆女神图集》(Mnemosyne Atlas)。在这图集里,他摆弄编织着雕塑、绘画甚至印刷品等一切“图像”(image),经由类似于“蒙太奇”的剪辑而成的各式“图版”,尝试去重建历史叙事中活生生的姿势与动作,带出人类历史机体中曾有的记忆世界。在这个图集的实验中,阿比•瓦尔堡不仅是一名描述图像历史的艺术史家,更是一名导演图像剧场的艺术家。他打开图像的“死结”,激活图像的视觉、姿势、意义的各个维度,把它们重新编织为新图像集。
编织,作为一种记忆的技艺,无所不在。从古代的结绳记事到今天的纤维艺术,人类参赞造化,宇宙在乎手,编织与拆解,只是试图不让自己的记忆成为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