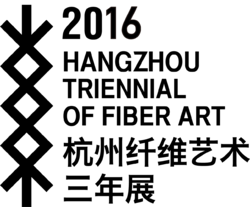1. 本世纪的拳坛对决。肌肉抖擞,一声咆哮响彻拳场。尤班克斯(Christopher Livingstone Eubanks,简称ChrisEubank,英国职业拳击手)大步走向拳台。一束追光紧跟着他,渐渐追上他的脚步,在他的头顶跃动,又照在他的前方。他身上穿的是什么。
一件垂膝宽袍,披风,还是长T恤?高科技医疗大褂,A字迷你夹克,还是希腊乡间长袍?粗边长巾,贴身罩裙,薄如蝉翼宽纱衣,玲珑剔透细布衫,纷纷籍籍流苏乱…… 似乎“雄赳赳的男性符号”变成了“软绵绵的女性符号”,又变回原样,好似两者之间有个织布的梭子,往复不已。非彼,非此,却仿佛同是彼此。我们面对着一件“不明确的服装”。
2. 一件“不可判定之物”,如德里达所说,即某物似乎属于某一体裁,却越出了这一体裁的界限,说它属于另一体裁也可成立。[1]我们也许可以说它同属两者,却不能专属于任何一者。我们是否应该将“织物艺术”视作这种变色龙般的“不可判定之物”?
3. 我们站在杜尚的作品《体裁寓言》前。[2]两种观看机制将我们牢牢地握在手心,使我们陷入两种体裁及其话语的僵局。一团纱布从画布上凸起,仿佛一朵云,将要撕破,飘离画布。一块抽丝的织物被团作一团,半是凹陷,半是肿胀。或许它曾是那种使领口、袖口坚挺的脆硬夹层,在熨衣时蒸发掉的闪光衬料——一码波纹绸,一种“可熔之物”。当我们看的时候,纱布仿佛脱离了自身,玩着自己的细线和纹路,“旋离自身的线团”。我们被要求以观看一幅绘画的方式注视它,它却没有颜料,没有染色。纱布呈现出它自身的形式与纹理的句法规则。它纯粹的“绘画性”震撼了我们。
那些所谓的“历史绘画”正是这种“纯粹形式主义”的反面。杜尚将这块纱布铺满、绷紧,塑成一种形状,好似乔治·华盛顿头像的轮廓,又像缀满星星的国旗,或浸透血迹的纱布,满是血污的绷带。这件作品诉说着战争的疤痕与创伤——国家,爱国主义,政治,正是从这样的暴力中雕刻出来的。纱布作为一种符号,代表着某种别的东西。杜尚以非常任意的、人为的方式将其与战争和冲突的概念相连,成为它们的“徽章”。它成为一种象征,激进地表现着某种不同于纱布本身的东西,激起另一种关联的湍流。我们处在寓言模式——一种符号的过剩。[3]
因此,在杜尚的作品中,纱布是一切,纵使它同时也是无物。它是一切,“赤裸裸的填料和织物”,引发视觉的活力,通向形式的终点。同时它又是无物,消解了自身,去扮演某种思想或观念的形象或符码,通向计划的终点。两种体裁相互抗衡,在无休无止的争斗中相互引用,又相互抵消。
4. “至尊家纺公司”——在我们眼前的照片中,一栋荒寂的红砖楼房几乎消失在视野的角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绍索尔(伦敦西部郊区),亦或在英国中部,甚至北部。楼前有一些亚洲女人,身披冬日外套,遮盖着贴身的传统纱丽/克米兹。对于那些来自印度旁遮普省的女人来说,从碧野无垠、尘土飞扬的乡间来到现代世界的中心,是怎样的一番旅程啊?她们有的举着标语,有的蜷缩在火边,火在一面鼓上燃起,这鼓成了临时的火盆。这是机械时代工人罢工的神话场景,标识着一个异见与抗拒的现场——指向工作、劳动与生产的条件。
无论“家纺”多么渴望“艺术品”的地位,它们依旧无法摆脱同制造与生产界的联系。装裱,上墙,展示,它们作为形式、色彩、纹理的告白,吸引我们的注意。它们含蓄的叙事力量令我们心神升华,却依旧不能使它们断绝与用途和功能的关联,会想到包裹,保暖,睡眠和舒适,一些壁炉和家的感觉。总之,想要忘记它们与加工、工艺和制造的关系也同样不易。
半在墙上,半在地面,它立/卧/悬于我们面前:日用品与艺术品的合一。家用商品同时也是观念的装置。被子立/卧/悬于我们面前,作为思索之物,却并未超越其朴素、平凡的本性。并非或此或彼,而是同为彼此,“不可判定”。
梅耶尔·魏斯曼,哈伊姆·斯坦巴赫,杰夫·昆斯——日常的消费品渴望艺术品的地位,同时又执着于自身的粗野与平凡?一件普通的棉布沙发床,在另一种语境中是否成了一个不同的物件,值得不一样的关注?难道被子不总是跨立于一个双重的编码空间,一个如此矛盾的现场?
5. 这似乎与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经典现代观念相左,对于后者,体裁应当清晰、自足,它们的边界被明确规定、严格审视。每种体裁都将自己缩减到其自身媒介的纹理和逻辑之中——抑制着溢出自身、进入另一体裁的冲动。
6. “哦,忙碌的织工,停下吧。一个词,为何需要这无穷无尽的劳动?片刻的言说。然而不,梭子在飞驰,形象浮现在织机上,在滚筒上,在染缸中,容不得片刻的打扰。你会说,生产愈发想要模仿永恒的运动,接近那使我们在此安身立命的自然之魂。工厂热火朝天的轰鸣震聋思考的我们。只在这时我们蕴含死亡。死亡编织着生命。我就是那个影像。我就是那张织毯。”[4]
7. 那些丝绸或许是在某个遥远的殖民地纺织而成,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种古老的技艺,服务于最为现代的用途。在大不列颠的某处,一包一包的丝绸被买来,缝成杯状,制成降落伞。这某处具体是何处?是谁将整个降落伞折边、缝合、接缝起来的?马上变成精巧的织物和强大的战争工具。既是神圣的布料,又是空军的军用材料——一把飘浮的巨伞,既能拯救生命,又危险致命。
作为战争的剩余物资,这些丝绸降落伞又变成结实的人工材料,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怎样在遥远的种族隔离地区被出售。它们在院子里铺开,就像一些受伤的、被打死的动物,最后一点气息,几下翻腾起伏,波浪状的形体被压平,在强劲的麻袋拼织而成的巨型地毯上铺展开来。我的祖母一丝不苟地割开那些丝绸,沿着确切的缝口和边沿,折叠处与接合处,一码又一码地“回收”,转作别的用途。
既是神圣的布料,又是战争用品,既救命又致命的工具——如今它们被迅速制成衬衫、裤子、裙子、纱丽,成为我们这些种族隔离地带居民的褴褛衣装。我们这些生活在种族隔离地带的被殖民主体不久便被称作“共和国公民”,继而作为“流亡者”而被驱逐,又作为“移民”而抵达,然后作为“非本国国民”,作为永远的“非公民”而生活——我们的归属便是没有归属,既非局内人,又非局外人,永远是“黑皮肤的外来居民”?[5]
织物艺术,难道我就是你?
注释
文章来源:詹尼斯·杰弗瑞斯(Janis Jefferies)编著,《重造织物》(第二卷:性别与身份)[Reinventing Textiles (Volume2: Gender and Identity)],(温彻斯特:Telos艺术出版社,2001),7-10页。
1. 雅克·德里达,《生活在边界》(“Living on borderlines”),收于《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75-176页。
2. 《体裁寓言》可以被形容为一件由纱布、钉子、碘酒和金星组成的集成艺术作品,现被巴黎私人收藏。
3.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174页。
4. 让·鲍德里亚,出处不详。
5.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与雅克·莫诺利(Jacques Monory),《叙事颤栗》(Récits Tremblants),119页。
萨拉·马哈拉吉(戴章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