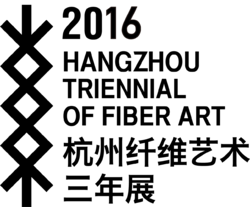为什么思考“织”的艺术,以及如何通过“织”进行艺术的工作?我们可以回望这样一种图景,这样一种感受:当我们站在现代工业的记忆场,历史中的织物、织造工具与双手将我们环抱其中——有来自远古的丝织残片,海上的水手的帆船结,绣有金色牡丹的黑丝绒旗袍、战时从天空落下的降落伞、台湾联福制衣厂的遗迹、码头上的因海风和雨水侵蚀后泛黄的帆布、祖父戴过的毛线帽——都带给我们对物质的认知、切身的情感体悟,也使我们目睹“织”的世界地图的流变。
或许在当下的知识语境和日常生活范畴里,对“织”的思考可能显得过于追古而不合时宜,或者继续为后殖民理论中的意底牢结无法挣脱式的“理论”沉醉,又或者是在日常中已经被规训的小资生活美学和小确幸而不自知。而我们今天所谈的“织”,与15世纪的秘鲁的织工所说的“织”一样吗?上世纪九十年代,洛桑双年展理事会决定关闭洛桑壁挂双年展,给出的原因是“人们对挂毯的兴趣在普遍降低,与此同时,纺织艺术领域的创造性也不如从前”,而我们重提是要唤起或焕发的是什么?
1971年在MoMA举行“超越工艺”之后,在这个“Beyond”所代表的之后和之外,是什么使其得以保留时间内涵?在1969年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的展览“织物中的视角”的近四十年之后,在杭州展示艺术的“织”,更新了哪些视角?
我想强调的是,重新审视当下个体与编织物之间的关系,是一切人与物质、地方、世界的关系的佐证,他们是“织”的社会遭遇,也是“织”之为一种象征的机遇。织,有其本身独立的认识本体和自治价值,这里关于织的创作与书写,不是深入机理地使用艺术或者参与进艺术,而是真正理解到“织”的艺术可以构织和经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织我在”一方面遁入以”织”为核心的工作起点,游走于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编织艺术;同时也将以“织”为核心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叙述状态和艺术创作的方法,编织进展览中。这是我们所提及的“织物式的”、“如织那般的”艺术的工作。
我相信,通过编织与织造获得价值感的个体与群体,都牢牢地与她所处的时代相连。
日常编织的前沿状态
谈及编织,我们要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前沿——这里是多元文化的复杂形式和社会生产的具体空间,它是劳动者、工坊和工厂的日常状态,也是民族分野之下每个个体的上手技能,这就是对“织”的认知框架的现场,是平常的、静默的、甚至是异常熟悉的。而正是在这样的日常之中,需要有一种警惕,上手与劳作并非是全然诗意和政治正确的存在,相反,编织是严苛的生存,编织的本能是对饱与暖的基本诉求;无论和平时期还是特殊时代,“织”都因意识存在的需要被赋予了现实意义。
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他们记录了一段往事,在这段往事中妇女、生产、解放和抗日通过纺织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时到达十里店的工作组准备成立一个妇女协会,以保护女性权益和提高生产为基本诉求。协会主席是55岁的王雪德,她是本村人,熟悉十里店的情况,也是很熟练的织布工。因为家里是中农,除了种地之外,家庭副业便是纺织。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就已经熟悉纺织这门手艺,当时仍是二十世纪初,乡村的手工织布还未受到城市织布机器化的冲击。但时代并不平静,父亲因为身穿和八路军相似的浅蓝色套装,被日本人枪杀,随即她的丈夫外出做生意,又被日本人抓走了,从此以后杳如黄鹤。后来,她经受不了婆婆的压迫和饥荒的折磨,成为十里店最早和最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人员之一。深谙村中情况的她,带着自己几乎快要废弃的纺织手艺,成为了新成立的妇女协会主席最合适的人选。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教妇女纺线织布。原材料和设备的款项由当时才成立的村合作社发放,技术由王雪德和几个精通纺织的姐妹负责支持。从16岁到50岁的所有妇女都符合条件,她们开展这种后勤工作,还能取得一定的报酬。十里店的妇女过去因缺乏本钱以及城市机器大生产的竞争而被迫失去职业,现在重拾这种技能并且能依靠这个技能继续生活。经济地位的改善成了十里店妇女开始解放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这给了我们一种角度思考“织”的面向。纺织是一种传承和传递下来的生存的技能,织物是供给现实生活基础的物质源泉——暖,是有温度的生存和生活;在特殊的战争时代,它还可以是一种社会的动力,也是一种被召唤出的群体存在的体现。而在现代性统筹的意识下,编织是女性自我解放的能量和勇气,还是抵抗他者、试图找回自身的一种途径。能让编织有所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特殊时期,自省与建构的姿态可以促生的创造。造,不仅是造物,也是造己。
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曾分享给我一部电影。Kanchivaram是一个印度的小镇,以丝织业闻名。欧洲人和印度的上等阶层都为这些纺织品而疯狂,每个人都希望能穿上这些手工织就的如星空一般闪亮的美好织物。但是有两类人却不能获得:一个是织造这些美丽织物的人,也就是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和他的家人——他是能织出最美沙丽的人,当女儿出嫁,他甚至不能为女儿织一身美丽的沙丽。然而禁令也阻止不了父爱的蔓延,也正是因此,伟大的匠人因为不可抑制的情感被送进监狱。他可以拥有看不见的技能,但却无法拥有看得见的物。
而另一批不能与这些美丽织物接触的人,则是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团体。高等消费法的管制下,这些纺织品的穿戴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欲望与禁令之间的张力。而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工厂的建立,终结了这样的渴望,也部分终结了织者的生活。印度以棉纺织国为傲,而英国机器大生产的棉纺产品对印度的“自由贸易”,更进一步夺去了织工的基本工作,也几乎浇息了印度的棉纺织业,“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的原野都漂白了”。甘地发起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非暴力方式抵制英国统治和英国商品,手纺车运动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旨在杜绝对英国纺织物的需求。甘地和他的追随者使用纺车自己纺布做衣服。把物的生产和使用都收归自己手中,即既要拥有物,也要有造物的权利和能力。
这样的编织,从社会思考的角度让我们着迷,充分展现了“织”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厚重的程度。
斗争作为一种联结
联结的踪迹,如纬线一样贯穿前四个维度。是摊开,是拥抱;是扭结,也是褶皱锁紧。通过联结织就的网,不仅是物质之网,还有语言之网、现实之网。编织也是尊重某个原则的组织。
陈界仁的《加工厂》是另一个Kanchivaram镇,工厂如同岛屿一样漂浮在全球生产链条之中,各个地区能产生的更低的成本,资本的流动,都是截断航线的剪刀。经由影像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曾经一度繁忙、紧张的工厂生活生产情景。工厂的集体生活,像是一个基地,为工人们套上生活的时间和方式。自1960年代开始,纺织业都是台湾创汇的重要产业。九十年代,随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台湾的密集劳力业开始外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区域,大量裁员和恶性关厂,导致无数劳工进入长期失业的困境。位于桃园的联福纺织、福昌纺织等数家工厂关闭。失业女工们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活动,而艺术家则是请女工们重回荒废了七年的工厂重新“工作”——灰尘漫溢,动作凝滞,不可移动。手中没有一针一线,却已经离不开习惯性的穿针引线动作;工厂成为宰制的象征、每一个熟悉的动作都可能是制服的衍生。
这是陈界仁的世界工厂地图的节点之一,也是抗争地图的场景之一,是自身和生活周遭的现实环境:七年来一直发生抗争的地方,也曾是供给自己一衣一食之地;法不在此的生命抵抗,夜以继日,无休无止。
交织,颜色
“我们关心的是色彩构成,即看到的色彩彼此之间发生的情况。色彩在不断流动,总是与不断变化的相邻色彩及不断变化的条件存在联系。”——《色彩构成》,约瑟夫•阿尔伯斯
一方面我们着重于织的技术、材质,另一方面,我们也本能地用基本语言描述视觉的呈现。比如颜色。
绿色,当我们说绿色的时候,50个人的脑海里就会呈现出50种不同的绿色:初春柳条的绿色,天鹅绒的绿色,池塘的绿色,青苔的绿色,巴西国旗的绿色,国画颜料里的藤黄花青,台湾政坛的深绿阵营……绿色,贯穿刘韡的系列作品“绿地”,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意识贯穿着整体的创作,颜色、材料、物,交叠可以产生的体验和意义,都在绿地中被重新集合在一起。刘韡提到过,帆布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代表着丛林和适者生存。帆布多是粗厚的棉织物或者麻织物,它的经纬纱均用多股线,并且采用平纹组织,经线和纬线浮沉交织而成,在一个组织循环内有两根经纱和两根纬纱进行交织,有两个经组织点和两个纬组织点。由于交织点很多,经纬线的抱和最为紧密,因此平纹织物的质地最为坚牢,外观最为平挺,最早都被用在驯兽、帆船上,且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机械化生产领域,如遮挡、阻隔、防水、提防、包裹、伪装等。
在作品《绿地》里,工厂一样的绿地,帆布的军绿色,泛黄的绿色帆布等,这些颜色,是我们对刘韡描述的世界的视觉判断和语言判断,颜色感知相对颜色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这也是我们对物最基本的描述方式。而墙一样的尺度,更加复杂的形式集合的抽象历史,让我们也直接产生了体感——帆布包裹的巨大框架结构,是一座座虚空的纪念碑,轻微的摇晃带来的不安全感,似乎引出工厂集体生活的记忆、集装箱码头的记忆,是一个个巨大的掩体构成的迷宫。
帆布所显现出的织造,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织造更像是机器和堆叠的产品。它可以反复提醒我们存在着一种规训之后的色彩感知和体积的冲击。在《绿地》要让我们发生触动的,是要让我们置身于织物与框架构成的去迷宫,去感受那个原本需要用政治经济学去讨论的现成生产场景,体会那种织造而成的绵延不绝、巨大、颤抖、拉紧与压迫。
对颜色的把玩,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精确严谨的方式。
阿尔伯斯带着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去到黑山和耶鲁,将色彩构成实现为一种用现成物随手拼贴的日常练习。跟随约瑟夫•阿尔伯斯的学习的希拉•习克斯深谙颜色的组合与心理,对于习克斯来说,色彩课程构成了她把玩所有材料的重要部分。那已经是近60年前的事情了,阿尔伯斯递给刚毕业的习克斯一份文件,是一份到南美游学的奖学金。阿尔伯斯告诉她,南美有你想要学习的东西。五六十年代的南美,是所有艺术类型的创作者的集市。小编织不仅是编织练习,也是创作的日课。线与线的交缠,颜色与颜色的关系,是习克斯的创作起点。七十年代在墨西哥的生活,随后在印度与织工同织同住,八十年代开始再到巴黎市中心隐居。她的编织也能清晰明了地让我们感受到颜色与周围环境相联系所产生的流动,这些色彩来自她所落脚的各个地方。在她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颜色的纠缠——热烈粉红点缀在天然棕色之中,艳丽的红色和深深的绿色相互交织。颜色的穿插,从整体视觉上提供了编织的开始、暂停、终止,像是一种韵律。颜色和颜色通过纤维材料的粘结,可以被解读为在这里,在那里,在上方,在下方,都可以解读成在空间中的色彩。
除了调配空间中的颜色,编织结构还能调整物的质感——经线在纬线不同的纠缠方式,让织物平面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交织的极致,艺术家也要不断反思模仿的逻辑、重复的逻辑。通过“编”,这个小小的无以数计的行为,通过使用的材料和其承载的意义,与心境交互发生作用,产生多重效果。
除开基本的棉麻毛线,希拉还向我们展示了许许多多材料的纠缠与拆散。羽毛、贝壳、报纸、樱桃棍儿等等,无论从材料还是观念的角度,她都在一直拓展纤维的可能和人们看待它的方式。这是她不断坚固对“织”的信仰的日常实验。无论材料使用天然棉还是高科技丝线,无论作品是色彩丰富还是颜色单一,她的独立雕塑、壁挂和纸上创作都超越了艺术、设计或工艺的类别。每一张小编织好像是种种来自艺术家的呓语,织就的不仅是时间,也让整个过程视觉化,我们看到的物品、材质、颜色,都是一个织者个人性的编织,使她同时成为画家、雕塑家、纺织家、色彩艺术家和诗人:
“我们深深依赖着交织的线。
我们穿着。
我们亲密地依存着。
我们欣赏着,我们需要他们。
线在空间中穿梭,
绕着我们的腿,缠着我们的脚,
环绕着我们运动着的身体。
我们住在里面:帐篷、窗帘、浴巾、荧幕。
面具。
把线拉紧,折弯、压紧,打结、锁边,去捕鱼,
拉一个索套,捕一只兔子。”
——希拉·习克斯
千针万线
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那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忠贞妻子,为了拒绝所有的追求者,宣称要为公公织完一匹做寿衣的布料,要等到这件以死亡为名的衣服完成之后,才会决定新的婚姻。于是,每个白天家里宾客不断,都看到佩涅罗佩在织布机上不停工作;而到了夜晚,宾客离开,这个智慧的女人则将白天的织就的部分全部拆掉,再等待第二天黎明的抵达,织才重新开始。黑夜,给了她拆解的帐幕,犹如面纱一般。对于所有人来说,这真是一次神奇的无终结的织。一方面考验了追求者的等待的魄力,一方面则是对编织的智慧历练。可以织,就也可以拆开;织的终结在于锁边,织的智慧在于,一日不锁边,这匹布料就不算完成。这条边好比是死亡的象征,以生命的终点作为编织的终点,这主动寻求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每一次织的重新开始,都是一次新的去路。
日常生活的编织美学就是其中一条路。只是我们要斟酌的是,影响当下回归上手的工艺、手工织物,或者是追求以手工和慢为美的生活美学热潮,其源头何在?织者对织的洞察和开拓来自自身的实践,或许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织”的主题,艺术家只是作为织者中的一支。
第一点是对织有所领悟、有所作为,通过“织”作用于个体的实际生存——“与肌肤最为亲密的“织”也一直在,我们本来就在,以“织”为类的群体只不过是通过“织”再次确认这个存在——在这样的历史长河里,当下的织者与15世纪的秘鲁织工是相同的,坚持经线纬线相交,并在此为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不断展开。
第二是“织”可以作为一种交流的语言,是从第一点上衍生出来的。在当下的通俗生活中,“织”通过艺术家、媒体、产品表现了出来,而这是一个丰富的实践领域,不同的地方和个人,都可以产生创造性实践。每一种“织”法、“织”物,都是把非常规的日常知识纳入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常规知识系统中去。许多织者也自我发愿,希望能够让一种古老的知识、在野的知识得以复苏。
这也引向了第三点,知识的复苏是内在复苏并拓展出去,首先是和自己打交道。很多人的出发点,不仅是智性的,更是情感的,是那种执迷、痴迷、痴情。在织的世界,这个区别于一般世俗世界的地方,情感是织的核心。
而第四点,编织着的工作者、参与织造的创作者,通过“织”告诉我们并且实现可能的思考方式,都将是我们看这个“织”的世界的途径,我们熟悉的编织艺术家,或者以“织”为作品的艺术家,以“织”为思考方式的艺术家,都成为了这场展览的叙述者。不可否认,“我织我在”中的呈现,是一次在“织”中思考的动员,参与者都变成了“织”的述说者、歌颂者和宣言者,也是预言者、劝诫者和遗忘者。可见,艺术家只是其中的一种角色,织者才是核心的主角。每一个个体与作品共同构成角色,也构成了身心互动的“我们”。
从织到识,从线到言
待我们把“织”的联结打开,可以看到多重的“织”的世界:波兰纤维艺术的辉煌时代不得绕开二战后社会主义进程中,为了树立国家形象,国家推崇特色手工艺,并且提供给艺术家对个人创造性的宠爱;南美与非洲的日常织物的诞生与消亡,联系着一个群体,或者一条海上织造之路的升起与没落;白俄罗斯毛毡靴厂的静默和台湾倒闭的制衣厂的静默则是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国际生产链条断裂所带来的重压;一个材料人如何试图用社会性企业的方式,将织物的启蒙带回生产的世界。从织到识,实际上是从物质和技术之线,到以针载言、以文作线的勾连过程。
以“织”为核扩散开去,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如果习惯在旧式的艺术史框架内思考,把艺术家分成流派,他们一直面对的是风格的差异,这好像是解决艺术具体问题的基础。而我在“织的艺术”,“织物的艺术”中所看到的,恰好有所差别。从内部去观察,也许恰好借鉴了织的方法——确实,编织的技法是识别一个艺术家的方法;而时代的材料与技术,提供给织者或艺术的织者可能的交织方式,足以让人耳目一新;而接下来,可能像是一个谜团,如何通过这些维度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织者的艺术——听他/她说话,看他/她前后的创作,这可能都是我们惯常的方式;穿过那个平面,每两根线交叉,可以形成很多个结;四根线两两相交,是一个格子,有大格子,也有无空隙的交缠,这是时间的密度、持续性和延展度。一块织物,我们剪掉织物的四边,我们看到的是千经万纬按照规则组织在一起,好比我们此刻通过展览去勾画的这张地图:有浙江袜业小镇大唐、八十年代北爱尔兰逐渐没落的亚麻产业、加纳女性拥有的荷兰印花布、危地马拉的编织、江苏镇湖的刺绣、六十年代引领时代的洛杉矶艺术学院教授的编织,杭州百年丝绸元泰……能织就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是每个个体、每个人群,以他们各自的编织方式,让我们也得以更接近“织”这个词的内核和更广义的存在。
致谢
谨以此文感谢我的策展伙伴,许嘉与阿萨杜尔,以及诸位导师。我还体会到了来自织物工作的同行(xing)者强有力的支持和智慧探讨;同样感谢与我协同思考的伙伴们,我从你们的身上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