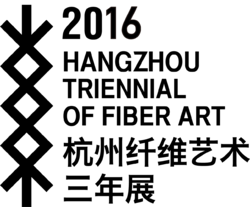织,古文为織。对于織,《说文》曰:“织,作布帛之总名也。”“经与纬相成曰织。”布,麻缕织就而成;帛,则指蚕丝织就而成。说明至少到东汉时,织的对象已不仅限于蚕丝,亦包括麻缕,只要是经纬相成的便可称为织。经,《说文》曰:“织从丝也。”从即直。“纬,织衡丝也。”衡即横。又曰:“经在轴,纬在杼。”“南北曰经,东西曰纬。”简而言之,就是纵向为经,横向为纬。有趣的是,古人称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而六经之书又谓之秘纬。通过这种经纬与纲常伦理、六经六艺的对应,织便自然地和经典相连,由此,织物艺术与中国文明也就牢牢联系在一起了。
从織的汉字结构看,分为左边的糸旁和右边的声部戠。糸,《说文解字》曰:“细丝也。丝者,蚕所吐也。细者,微也。象束丝之形。”又“蚕曰丝,麻曰缕。缕者,线也。”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线,包含了蚕之丝和麻之缕,织既为糸旁,说明它最初的对象为丝,不过至少到东汉就扩展到麻缕了。因此,汉字本身,便蕴藏了中国为丝之古国的讯息。
织的词组通常也都是糸旁,和丝有关,编织,纺织,织纴,织绣。编,“次简也。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即按一定顺序用丝线将竹简串联排列。纺,“网丝也。丝之纺,犹布缕之绩缉也”。纴,“机缕也。左传鲁赂楚以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绣,“五采备也。《考工记》:画绘之事集五采,五采备谓之绣。按今人以针缕所紩者谓之绣”。编,纺,纴,绣,与竹简,与绷架,与机器,与针剪,丝线成为书籍、衣饰、锦缎、刺绣的基本元素,织也就此进入文学、服饰、时尚、工艺及艺术领域。这些或徒手,或执针,或使用机器将丝织就在一起的劳作述说出中国人最早的日常生活中就与织物紧密相连。不论是平民百姓的布帛粗服,高官显贵的锦衣绣裳,还是文人大夫的篇简笺书,闺秀青楼的绣画绢扇,织作为人的一类生活方式,上至高雅艺术,下达日常生产,将国人的温润与情愫以绵密而生生不息的形态缀在了一起。
至于戠,《说文》认为“从戈从音”,本义阙如。“音”指古代军阵操练时教官的声音,“戈”为参加操练的军士及其武器,二者联合起来即表示“军队方阵随着指令形成各种队列图形”,所以,戠可以会意为规则图形及其变换。《说文》亦曰:“戠,聚会也。”如此看来,戠不仅是声部,亦表动作。仅仅“織”的汉字结构,便意味着它的对象为细丝,动作为汇聚形成规则图形及其变换。
在织指向的众多劳作中,与衣饰的关系最为密切。衣,带给人温暖的体感,饰,象征身份的高低,于是,织首先与人的身体,进而与身份,即家族发生关系。也正是织与身体及身份的联系,会让人们发出织物为人类万艺之母的感叹。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耕女织,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女织,是妇女四德的妇功中最重要的一项劳作,它的时间性和重复性象征着母性繁殖的力量。不论手织,针织,还是机织,织机与双手日夜不停地重复劳动,天经地纬,织成万物,如同妇女不断地生育繁殖,代代相传,这种母亲本源性的创造力源于大自然的赋予,却又不断地推进着人类自身的文明演进。
本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的主题“我织我在”,即是从织的本源出发,却远远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织。首先,“织”指向“在”,它同时可作名词和动词。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无论织怎样变化发展,从最初的手织到工具出现后的针织,到工业化时代的机织,再到今天的数码编织,所有这些织都指向一种本源,即人的存在。如江南的缂丝,北方的缂毛,缂织材料粗细软硬不同的表面下其实隐含着不同地域环境中人之内涵的迥异。所以,无论“织”的手段怎样被提升,被超越,都毫无疑问地指向“在”,人的存在。“织”不是某种既成物,而是生生不息的动作与创举。这种生生不息之举在,人在。
其次,“我织我在”从一个角度述说了技道相生的秘密。我织,是技,我在,为道。艺术的技艺是一门手的技艺,织亦是如此。通过手对独特材料与工具的掌握和运作展示材料的独特性能和魅力,是手工技艺的特殊品质。所谓“劳作上手”,即凝练旷日持久的劳作,让某种独特的方法和技术留在手上,形成独到的身体记忆和即时反应。这种“劳作上手”成为艺术的风格之基。绘画是笔墨挥洒在绢纸之上的“手之技”,雕塑是斧斤敲打在金石之上的“手之技”,织则是针线织机穿梭于经纬丝缕之间的“手之技”。道在技之中,仅在技之中。“我在”在“我织”之中,只在“我织”之中。技与道不可分,佝伛承蜩,斫鼻不伤,公输刻凤,点睛飞去,均是技近乎道之例,后二者虽然有夸张神话之意,但都意在说明技可通道、道可养技之理。技近乎道,我织,故我在。
无疑,用纤维艺术这一既带着温暖柔软的记忆又潜藏着生长繁殖的力量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织我在”,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为贴切的了。英语中,并没有一个单词对应汉字“织”,均需要构成词组来翻译,如编织译为weaving,纺织译为spinning,织绣译为embroidery,织物译为textile或fabric。英文的主题表达选择用weaving,是因为它即表示名词,亦可为动词,这和中文中的“织”相应和。双手的编织可谓“织”最初的形式,手与丝线的摩擦触发身体的各种感知。“我”既是存在的主体,又是劳作的主体,也是思考的主体。英文中决定采用复数“we”,一是读音上押韵,二是强调“织”不仅与织者、艺术家相关,其实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不仅代表着一种“织”的形式化图案,更表达了中文主题“我织我在”背后的那种“织”与“每一个人”的休戚相连的生存关系。
既然是对生生不息的存在的叩问,艺术作品就势必要回返生活本源。本届三年展中,艺术家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这种回返。他们或是回返生态,如中国艺术家梁绍基的创作始终以蚕为主题,蚕茧、蚕虫、蚕丝,通过生物实验来传达生命的周转和自然的神秘,以此来阐述艺术家关于时间、呼吸、运动、宇宙、精神、永恒的感悟;中国建筑师陈浩如用来自安吉的毛竹建构起一座乡土生态丛林,它以编织作为结构和形式的语言,从二维进入三维进而营造出一处场所,汇集成人群活动的场景;美籍华裔艺术家刘北立从一个个蚕茧中拉出的蚕丝变幻成沐浴在阳光下流动不一的云朵,并运用蓝晒法用自然光赋予云朵深浅不一的天然色调,回应传说中“女娲补天”的壮举;意大利艺术家克劳迪娅·罗西此次以在地创作艺术家的身份,通过工作坊的传递与交流,将中国文化中的神话动物以及现实中的多种动物特色与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动物世界相关联,创造出了一组造型生动诡异的动物群,以表达庞大世界语序中生物的相互适应性,并取名《邻近》。
纤维与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合二为一将其视为第二层皮肤。在这次展览中,“纽曼/供使用” 小组的《管道·杭州》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纤维与人的密切体验。织网世界让我们身处其中,身临蚕蛹被蚕丝缚束的体触,同时又体验到那种柔性的力量与身体相碰撞时的与身俱来的依恋;大厅中美国艺术家希拉·习克斯的《纤云弄巧》,用一堆堆彩色线团自由地构成柔软可变的雕塑群,观众可以走入场景中触摸、翻滚、抛掷,体验由柔软的纤维带来的温暖、惬意与安全感。
有一些艺术作品则是记忆的重现,出生于北爱尔兰的加拿大艺术家利西亚·丹妮·特劳顿将头发刺绣在亚麻手绢上,树立起一座座纪念在北爱尔兰问题中死去的人们的“柔软的纪念碑”;比利时艺术家海蒂·芙欧特用彩色塑料带创作已经消失的国家的国旗,以这种500年为轮回的媒介和手段去探索人类文明过去500年的历史;来自加纳的英籍艺术家戈弗莱德·邓科通过他的母亲来讲述在荷兰生产出口到西非的传统布料,这些彩色“货币”的流通在传达商品、金钱与知识流通的同时,展现了加纳文化中有趣的命名传统。
另一批艺术作品指向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影像作品《加工厂》通过请制衣厂女工重回已经荒废七年的车间工作,用黑白宣传片的形式记录下当年“停滞”的残余物和今天“流动”的劳工,反映了台湾工业外移后失业劳工面对的残酷处境;将织机做一次新的编织,是艺术家许江和袁柳军的新作《山水离歌》,曾经的母体——袜机,被它的产物袜子像茧一般地包裹,艺术家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浙江诸暨大塘镇早期产业的凭吊,而是某种被这飞速变迁所塑造、并依然日复一日被塑造着的现代物化的感性经验,老织机被软化为一种梦,一种产业乡土的复杂交织着的乡愁,并向外传递着一种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发生着的诗化的转型,这是现代织业的离歌,这是真实的工业山水。
英国艺术家詹尼斯·杰弗里斯以一组数字化技术呈现的照片,展示了海宁印染企业机器运转背后的纺织工人鲜为人知的辛劳工作;白俄罗斯艺术家维克托·阿斯留克用镜头记录东欧小镇冬日人们充满律动和温暖的劳作;美国艺术家塔里·温伯格则用刺绣在绸纱上的红线暗喻流水线上的女工身体,揭示从这些女工身体中所体验到的社会变革以及肉身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关联。几位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段和视角记录了东西方纺织制造业背后的故事。在专项文献单元“绣画掇英”中,策划者向观众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卓著的绣画艺术,但同时也提出了今日的苏州绣画——刺绣艺术之乡的镇湖,在数字图像时代的商品化浪潮中面临挑战和变革。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生产重要的纺织业和第一现场,它折射出的是众多向度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批艺术作品注重从媒介的角度切入,英国艺术家法比奥·拉塔兹·安第诺瑞用特殊印刷纸与涂料织就了一面记录了雷曼兄弟公司故事的双面传感旗帜,每一次触碰对应一组股市数据,观众的手在作品表面的滑过即化作时代的歌声;中国的年轻艺术家王志鹏用视屏建构起一个无形的空间“场域”,通过数字捕捉定位编织出我们此刻的存在;韩国艺术家金守子以人喻针,她穿行在时有暴力和冲突发生的不同城市中,将自己定位为一根以愈合为隐喻的“针”,表现特定城市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宗教、殖民与现实;生于哥伦比亚的英国艺术家奥斯卡·穆里洛则选择了跨国界的小学生的课桌为媒介,孩子们在被包裹了一层白色布面的课桌上自由地记录下校内校外每天生活的点滴和梦想,画布成为叠加时间记忆的彩色镜头,固定下孩子们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现场。艺术家以编织为隐喻,通过这种现场即兴记录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交织在了一起,将儿童这一群体带入了社会叙述的视野。
1985年我跟随保加利亚艺术家万曼先生学习现代壁挂,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采用纸浆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元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纤维艺术工作者。然而,我欣喜地注意到,本届三年展的参展艺术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织物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外,还包括活跃在国际艺坛的当代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跨媒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这也代表着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虽然主题从第一届的开放观念下的“纤维,作为一种眼光” 回归到本届的聚焦纤维艺术本源与本体语言的“我织我在”,但实际上,参展作品却越来越呈现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拓宽了传统概念下的“纤维艺术”的定义。这无论对三年展,还是对纤维艺术本身,都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消息。
施慧
201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