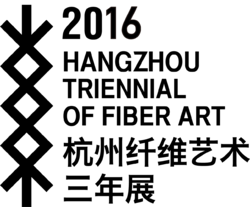-
织世界——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序
1947年,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言:“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近日,英国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却视中国为水的文明,认为水渗入从日常生活到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因此产生了“在水利工程、统治、清廉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之间(形成了)一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我要说:织在中国也有着特殊的意义。织不仅是“布帛之总名”,而且,经与纬相成,成为操持诸事的识度和方法。所谓经纬分明之幽微,所谓整经做纬之操习,所谓经天纬地之广袤。织的形态作为裹身之衣帛到思衬的繁密,包涵了从人的颜面到人的内心,让人特别有切身之感。

-
纵横交错织造乾坤 ——2016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前言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学会了利用纤维。编草为衣、结绳记事,都是以纤维为载体的人类技艺。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与纤维息息关联。而把纤维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则要晚得多;特别是作为当代艺术范畴的纤维艺术,直到二十世纪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是一门既古老又现代的艺术门类,集古典与现代、浪漫与沉稳、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手工编织于一体,既兼具绘画和雕塑的表现功能,又突出平面和立体的形态特征,具有独特的视觉美和触觉美,不断给观众以全新的审美体验。现代纤维艺术在不同的领域发展和壮大,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并向公共艺术和现实生活拓展,展现出无限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
梁绍基:面向艺术与科学的新界面
梁绍基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为特立独行、难以捉摸、甚至古怪的人物之一。他以非凡的热忱与痴迷投入到与那些极不寻常的搭档——蚕的工作中已长达三十年。
-
许嘉:为什么谈“绣画”?
刺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曾经一度与绘画并驾齐驱,上古时,天子裘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就实行“上衣下裳,衣绣裳绘”的传统。直到今天,刺绣仍作为一种被大众喜爱的有质感、有温度的文化方式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数字图像时代、网络社会、快生活节奏的商品化浪潮中,以“技”、“慢”、“工”为特点的刺绣的传承和发展遇到了诸多问题。在所谓的“今日刺绣之乡”苏州镇湖,排线凌乱、针脚极粗、配色俗艳、粗制滥造的十元一幅的机绣作品充斥坊间,却成为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热销品,代表着今日刺绣成为国内外游客对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的最常规记忆。表面上,传统刺绣通过如此现代工艺得以延续,可实质上,其文化内涵被忽视,丧失了真正的活力。而要保持并延续刺绣的当代活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建刺绣的“艺”,而非“技”的文化内涵。“绣画”的命题正是来源于刺绣与绘画二者文化内涵的溯源比较,来剖析刺绣的艺之本质,从而探讨今日绣艺之发展。
-
不舍一针一线,一丝一缕,不弃一个念头,一个主意的Claudia Losi |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我致力于将人和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我的创作主旨,以及通过旅行和探索作为知识经验。”
-
以房间为创作原点的Ismini Samandidou&Simon Barker|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以“房间”为创作原点解构 人类关系和政治的联系
-
单亲妈妈又是毛线轰炸之母的Magda Sayag |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要诱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非传统的、有趣的地方”
-
从关于意义和概念的辨证里抽离出来的胡晓媛 |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从关于意义和概念的辨证里抽离出来, 联系着她从日常事物中获得的微妙体验”
-
从收藏家变成严肃职业艺术家的Claire Zeisler |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载斯勒是打结和缠绕的纤维的的使者,她创建了多维形式的织物和强大的体量,古老的技术在她手中已经找到了新的语言,和新的意义”
-
探讨社会中个体如何发展的 Adelina Popnedeleva | 我织我在▷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参展艺术家
Adelina Popnedeleva在她的表演与录像作品里,用到了非常多的日常生活材料。在艺术家的一份自述里,她提到,“我的作品都由现实生活的各种挑衅,艺术本身也是危险的”。在她的诸多表演中,“我想给观众看我的灵魂”。所以时常有不少都是心理表现。